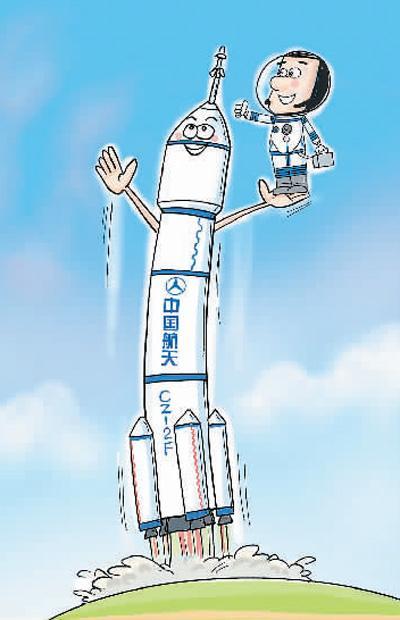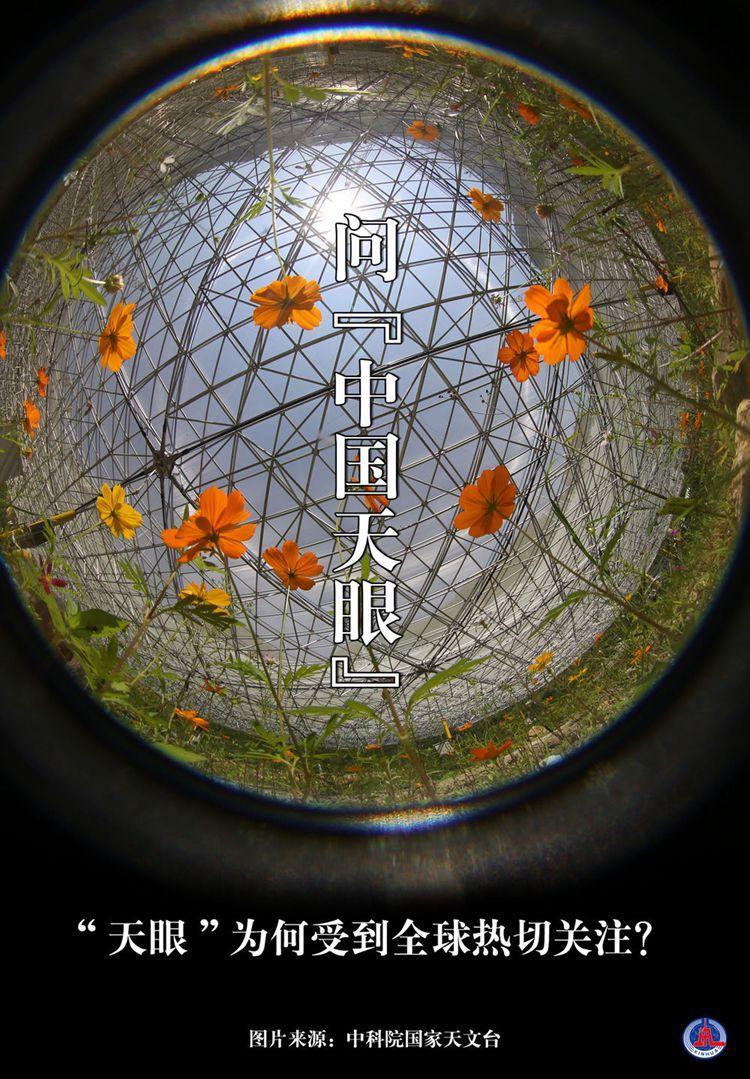西周之谜:中华文明的关键一步
发于2023.6.12第总第1095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公元前1059年5月下旬,岐山脚下的人们仰头看到了“赤乌降临”。那一天,水、金、火、木、土五大行星聚集在西北的一小片天空中。这是种罕见的天象,3000多年后,天文学家追踪证实了那一年的“异象”,这种天象516年才发生一次。
看到异象的人是周族的人,姓姬,生活在岐山下的岐邑。百年前,他们的首领古公亶父带领族人踏上征途,来此定居,建立了属于自己族人的城邦。他们现在的首领叫姬昌,是古公亶父的孙子。
经历三代首领的经营,周人将岐邑建设得越发强盛,人口稳步提升。当时最强大的政权是位于今天中原殷墟的商朝,周人则偏居在遥远的西部,有山河阻隔,商人称他们为西岐。周人臣服于商朝,出土的甲骨文显示周人祭祀的时候,还会祭奠商人祖先和最近死去的商王。不过,商朝的纣王非常残暴昏庸,沉溺于酒池肉林,不理朝政,百姓民不聊生。
这次天象震撼了周人。他们隐隐觉得,这是不是一种神秘力量的召唤?或许是天命降临?
姬昌随即称王,宣布脱离商朝统治。在“天命”的召唤下,周人开启了征战之路,统治区域不断扩张。文王去世后,公元前1046年,其子周武王率领西土部落联盟东征,冬天时抵达洛阳北部的黄河边,跨过黄河,直扑商都。公元前1046年2月,西岐远征军在商郊牧野与商人全面交战。战斗异常惨烈,持续了一天一夜,次日日出时,周人大获全胜。商纣王自焚身亡,西周建立。
陕西临潼1976年出土的武王征商簋(又名利簋)铭文记载了牧野之战:“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右)事(史)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寥寥4行33字,惊心动魄。这只簋与《封神演义》的故事存在于同一时期,如今在国家博物馆可以见到真身。
今天,在关中平原西部的陕西宝鸡,岐山的地名,数千年未变。岐作为地名,在这里随处可见。在历史上,“岐”这个字与周朝密切相关,这里的周原遗址,散布着周人的大量遗迹。
与以残暴著称的商朝相比,周朝仿佛进入另一个文明的次元。几百年后,东周鲁国的孔子念念不忘的那个礼乐昌明、政通人和的时代,正是以文王、周公代表的先周晚期和西周早、中期。在后世,“周制”留下一个令人怀想的政体模式。周人更加娴熟地使用起语言和文字,系统地撰写历史、以诗言志,他们留下的故事和诗歌,至今仍不难读解。及至东周,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如熔岩喷发,达到令人困惑的高度。而这一切的一切,距离杀人献祭、神秘荒蛮的商朝,不过一步之遥。
西周肇建并不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普通的改朝换代,而是一次文化上的跃升。从商到周,政治、哲学、文化等各层面改天换地。如历史学家许倬云所说,周代的建立并不只是常见的朝代递嬗,也是整个文化体系与政治秩序的重新组合,从此奠定了中国文化系统的一些基本特色。他总结:“西周以蕞尔小国取代商,崛起渭上,开八百年基业,肇华夏意识端倪,创华夏文化本体,成华夏社会基石。”
谜团重重的商周巨变是如何发生的?
史诗级逆袭
这段遥远而缥缈的历史,在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下,今天并非遥不可及。
2020年到2021年,在陕西宝鸡岐山县的王家嘴村西北,周原考古队发现了一座夯土建筑的基址。基址坐北朝南,面积超过2200平方米,是前堂后室的两进四合院式建筑。通过地层学、器物学分析后,考古工作者得出结论:这可能是周原遗址目前可以确认的第一座先周时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
先周,指的是周人在武王灭商、建立西周王朝之前的历史时期,从古公亶父到周文王都属于先周。也就是说,先周是周人发迹的时期,周原遗址很有可能就是岐邑。
为了这个“先周首个”,考古工作者已经陆续奋斗了大半个世纪。
寻找先周,始于上世纪30年代的宝鸡斗鸡台,兴盛于周原。1976年2月,岐山县凤雏村生产队社员平整土地时,发现了大量坚硬的红烧土和墙皮。考古队随后启动发掘,一处大型建筑基址浮出水面,编号为“甲组(宗庙)建筑基址”。从上往下一共有四个文化层,最底层正是西周时期。凤雏甲组拉开了周原大范围考古的序幕。
甲组基址一共1469平方米,中线依次分布着门道、前堂和过廊,东西两边配置门房、厢房,像一套标准四合院。除了宏大的建筑,甲组基址还有一个重大发现:在西厢房第二室的窖穴中,出土了1.7万多件(片)甲骨,其中282片上有刻辞。这是殷墟之外规模最大的一次甲骨发现。
那时候,因为岐山这个名字,附近一直被推测是古岐邑的所在,但没有证据。一些考古学者认为,凤雏村的发现基本确证了岐邑的中心位置。甲组基址是一处高等级建筑,这不禁惹人遐想:它会是周王的宫殿吗?至今仍有人认为,它就是文王的宅院,可称为“文王大宅”。
但考古总是小心翼翼,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根据考古分析,凤雏甲组并不能确认为先周时期,而西周特征则很明显。在现实中,物质的使用周期往往横跨人为划定的时代,这处建筑有可能从先周一直使用到西周,但半个世纪前的考古工作没有给我们留下足够的线索。参与周原考古10年并在2016年担任考古领队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宋江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遗憾的是,在当时的考古工作条件下,很多信息没有搜集,导致现在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而宋江宁认为,凤雏甲组可能不是文王的宫殿,它的厢房多且小,居住的特点似乎更突出一些。根据越来越多的周原建筑遗存发现,现阶段很难指认周王的宫室,更无法确认哪座建筑就是文王住过的。
周原位于今天陕西关中西部,考古学界定义的周原有广、狭之别。狭义的周原指今天扶风、岐山两县的北部,东西宽约6公里,南北长约5公里。广义的周原则指关中平原西部,渭河之北、岐山以南的狭长区域,东西绵延余70公里,南北宽约20余公里,土厚水沛,自古就是理想的栖居之地。
3000多年前,生存在今天陕西北部地区的周人受到少数民族戎狄的骚扰,古公亶父带领族人向西迁徙时,走到岐山下,见到这片土地肥沃繁盛,生长的苦菜都是甜的。《诗经·大雅·绵》被认为是周人的史诗,记录了这段传说,“周原膴膴,堇荼如饴”,他们很满意,于是“曰止曰时,筑室于兹”,就此定居,命名周原。
周原是中国考古版图上的一个重要区域,也是解读中国历史的一个迷人的切口。1976年之后,考古队于1999年、2014年几次重返周原,重启大规模发掘,寻找岐邑这个目标贯穿始终。周原遗址是全国商周时期出土青铜器最多的遗址,数量达上千件,超过殷墟,其中大盂鼎、小盂鼎、墙盘、毛公鼎等重器以长篇铭文闻名。周原出土的万余片甲骨,数量仅次于殷墟;现已探明100多座单体夯土建筑遗迹,为全国西周遗址之最。然而,这些证据还难以证明岐邑的所在,因为缺乏先周的有力证据。
2003年12月,考古队在周原遗址以西30公里的岐山周公庙遗址作野外调查时,在一个废弃的水渠里,北京大学考古专家徐天进偶然看见了一个小骨片,用手一擦,赫然有字。次年春天,考古人员顺藤摸瓜,在水渠边找到了一个埋藏着密密麻麻甲骨的坑,挖出来的第一片卜甲上,开头两个字就是“周公”。周公庙甲骨上一共辨认出400多个字,出镜率最高的名字就是周公。随后在一片野枣树林里,考古队又发现了22座大墓,其中10座有4条墓道、4座有3条墓道,而西周诸侯国国君的墓葬只有一或两条墓道。这些更高规格的墓葬主人不禁引人猜测:会是周王吗?但学者的普遍观点是,周公庙遗址应该是周公的采邑——即国君赐给卿大夫世禄的田地,那些大墓不是周天子的墓,而是周公家族的墓。
寻找岐邑仍在继续。2004年,考古人员在周公庙遗址以西10公里的凤翔县水沟遗址有了新发现,发现了周长4000余米的城墙,是目前所知西周最大的城,城内也有大型宫殿基址。随后,他们以周公庙为中心,四处出击,在蒋家庙又发现一座军事防御性质的周城,在周公庙之西发现了铸铜作坊……
迄今,考古人员在周原遗址发现了4片建筑区域,凤雏村和王家嘴村都在其中。如今王家嘴先周遗存的确认,为岐邑的证实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证据。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徐良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考古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找到每一个时代的大聚落或者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目前来看,通过诸多发现,我认为王家嘴这一带应该是当时先周文化区内最高等级的中心。如果我们认为古公亶父迁岐这个事是可信的话,(王家嘴)这个地方应该是最有可能的。”
周文王在岐邑称王后,十年内似乎征服了居住在渭河流域的大部分商人族群,建立起周人的区域性霸权。他们逐渐东进,进攻了晋南的一些小国,距离商朝都城已经不远。文王去世前不久,在关中平原的中心位置建立“丰”作为新的都城,将势力从渭水西部的周原悄然东移。
文王去世后,其子姬发继承翦商大业成为武王,为父守丧三年后,武王率西土武装东征,完成灭商的最后一击。据《史记》的说法,商纣王聚集起70万军队迎战,武王的武装只有四五万人,但在牧野的凛冬时节,商人都无心为暴虐的纣王作战,纷纷倒戈,商王朝葬送于周人远征军之手。在后来与此有关的神话小说《封神演义》中,杨戬、哪吒、雷震子等人物都位列西土军队之中。
在商朝,周只是一个偏居西部边陲的少数民族聚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与中央王权都没有可比性。这样一个小国,为何产生灭商的理想,又如何实现翦商大业,令人好奇。这是西周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历史学家许倬云是西周史专家,著有《西周史》,他研究的重点,就是西周从一个蕞小的部落,如何发展成为一个国家,而且建构了超越国家的封建秩序。
而正是这套秩序,无意间铸成了华夏社会的基石。
西土联盟与天下分封
如果以《诗经》中的说法,周人灭商的战略规划始于文王的爷爷古公亶父,“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凭借在西部地区三代首领的经营,周人势力虽然逐步强大,但与商王朝相比仍然难以抗衡。当时周是商的附庸国,据文献记载,纣王曾听信谗言拘禁过周文王,于是才有司马迁“文王拘而演周易”的说法;周原甲骨卜辞里也记载过,商王朝曾经讨伐过周。可见,商对周有碾压之势。
周人卧薪尝胆、厚积薄发,但为了灭商,依靠自己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他们还需要一股别的力量加持。商朝西陲活跃着很多古老的少数民族,《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十一年,联合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方国部族,对阵商郊牧野。这就是西土联盟。
联盟的格局,延续到了西周建立之后。周朝并不像商朝那样以吞并的形式实现统治,而是让各方国部族各自回到故土,保持自己的特色。
历史记载得到了考古的呼应。西周考古呈现出非常独特的面貌,是一种百花齐放的多次级区域中心布局。在西周都城遗址之外,遍布各地的诸侯国遗址不断带来惊喜。西周考古中大量发现的高等级遗迹遗物,都属于世袭贵族家族,如山西曲沃晋侯家族墓地、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平顶山市应侯墓地、北京房山琉璃河燕侯墓地、河北邢台邢国墓地、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墓地、西安张家坡井叔家族墓地、山西绛县倗伯家族墓地、山西翼城大河口霸伯家族墓地、山西黎城黎国墓地、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迄今为止,考古已经证实了晋、燕、虢、鲁、齐、应、邢、滕、陈、宋、蒋、卫等西周封国的所在。
西周为何有这么多封国?
回到西周开国之初,武王克商之后,并没有立刻占领商朝都城自居,而是率主力部队西归。被征服的商朝遗民仍交给纣王之子武庚管理,武王留下三个弟弟管叔、蔡叔、霍叔驻扎在商旧都附近,监督武庚。两年后武王去世,幼子成王年幼,武王的另一个弟弟周公摄政,管叔、蔡叔、霍叔不服,联合武庚发动叛乱。随后,周公联合西周宗室召公东征,平定叛乱。之后三年,周公再次攻下商旧都,并且征服了整个东部平原,将西周领地向东推进到山东半岛。
正是这次周公东征,而非武王伐纣,真正开启了西周的政治建构大业。
为了管理东部平原和其他王国边缘的战略要地,周王室成员和亲属被派到各地建立封国,战国时期的历史学家将这种制度命名为:封建。西周开国元勋姜尚——即传说中的姜子牙——受封于今天淄博附近,建立齐国;周公受封于今天曲阜的鲁国,由于要在国都辅佐成王,派长子伯禽代为赴任;燕国在今天的北京西郊房山,是北京近3000年建城史的起点……这些封国是西周王朝强有力的触角,牢牢稳固了王朝对广大领土的统治。“西周国家在其征服的每一个角落都植入了周的成分,以作为统一政权管理的一部分。”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西周史学者李峰认为,“(这些变化)决定了中国华北平原随后几个世纪里的基本政治结构。”
这种政治格局正是源自周人龙兴的特殊经历。周人小国寡民僻居西部,面对东部的广土众民,必须设计一套统治机制——“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制度。许倬云说,这一封建制度,包括两个举措:一是分封子弟与亲戚,在紧要的地点戍守,彼此援助,构成一个庞大的控制网络;二是笼络不同文化的族群,寻求合作。
考古发现提供了佐证。迄今为止,周王室的遗存都是一个谜团。在普遍认同的西周三个都城遗址——周原、丰镐与成周,出土的基本是高等级贵族家族遗留下的遗存。丰镐遗址迄今所见最高等级的遗存,是西周贵族家族井叔家族的墓地;周原的高等级建筑和大量青铜器窖藏,基本也都与贵族家族有关;洛阳成周遗址考古所见的,也是周人和殷商遗民的贵族墓地,与王室密切的文化遗存很难见到。
这说明,周王权的存在感远不如商,王权留下的遗存也就稀少了,这些现象支撑了周王作为天下“共主”的说法。徐良高认为,这种商周政治体制的差异,可能就是后来中国历史上常常争论不已的 “周制 ”与 “秦制 ”两种不同政治理念与体制的历史根源。东周时期周王权衰落,诸侯并争、诸雄争霸的历史原因,也可以追溯到此。
做周原考古的宋江宁到殷墟考察时,就像西部小城岐邑的百姓进了首都,第一印象便被商都的壮观所折服。商是资源高度集中于首都的国家,“就像法国被称为巴黎和巴黎之外,商也可以分为殷墟和殷墟之外,”宋江宁说,“整个商王朝的GDP肯定比不过西周,但殷墟GDP会超过西周的每一个城市。”
地理角度为周的逆袭提供了另一个解释。从周人克商开始,来自西部关中的政治集团取代东部政治集团的变革,在中国历史上不断重演。秦灭六国,楚汉之争,北周灭北齐,隋唐建立……这一系列由弱者厚积薄发造就的王朝更迭,都是这一经典模式的复现,而以周代商是第一次。原因在于,关中平原这片神奇的土地,西起宝鸡、东至潼关,在黄河、秦岭等山河环抱之中,拥有天然的军事屏障,而渭河、泾河冲积的平原提供了北方难得的沃土,形成这些弱势族群在安全的环境中默默积蓄势力的理想温床。彼时,周人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自然禀赋的优势作用,但若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不难清晰地看出这一点。
对商周之际剧变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近一百年前,王国维曾在《殷周制度论》中断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他认为,周人与商人最重要的制度差异,一是立子立嫡之制,从而产生宗法及丧服之制,以及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是庙数之制;三是同姓不婚之制。这些制度是周管理天下的纲纪,旨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有人赞同这一论述,也有人认为,周对商的承袭大于革命。两种观点至今争论不休。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西周史学者李峰认为,如果一定要说周代的创举,应该是西周的行政体制。西周的官僚制可以按照行政理性和具体的行政需要来运作,这对后来中国历史的影响非常深刻。
不同于商依靠霸权和宗教维系统治,正规的政府管理开始在西周出现。到西周中期,基本形成了具有官僚形态的政府体制,主要包括卿事寮、太史寮、王家三大系统。最重要的成就是“寮”这种机构,寮不是具体官职,而相当于常设的行政机构,能把不同官员放在这个机构里,反映了当时周人对政府基本行政功能已经有分类的概念。“寮”本身的字义,象征宫殿里面有火,火意味着灯火通明,反映的是日常不间断的行政职能。中国最早的政府由此诞生。
殷鉴不远:周的反思
不仅后世为周人灭商的历史所不解,连周人自己也很意外。
为什么周能灭掉商?周人何以配得上这天下?他们希望找到一种解释,同时也是在建立一种正统性。《尚书》中几篇写于周初的文献里,记载了灭商之初周人对这段历史的求索和解释。他们最后相信,是“天命靡常,惟德是亲”的道理让他们继承大统,将商人失国归咎于德行败坏,罪名包括酗酒、荒淫、不恤民力……《诗经·大雅·荡》记下了振聋发聩的名句:“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周人发现,商朝的倾覆与夏朝近乎于原样复刻,他们终于领悟,这便是“天命”的规律。
周人极具反思精神,譬如他们认为嗜酒是商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便颁布禁酒令。青铜觚、爵、斝这些酒器,在商朝礼制中居于中心地位,周朝则以鼎、簋等食器取而代之,考古证据与文献记载完全吻合。殷鉴不远,周人处处以商人失国的教训警戒着自己。
当他们追溯到公元前1059年那次“赤乌降临”的异象,便追认为那就是受命于天的征兆,文王立国、武王伐纣是替天行道。后世学者普遍将“天命”概念视为周人的一项重大发明,与商人的“上帝”相对立。商人并不尊崇天,他们尊崇“帝”,“帝”是商族的保护神,源于商部落的祖先崇拜。“作为赋予了人性的神的‘天’——宇宙的终极力量,这看上去无疑是周人的一个发现。”李峰说。
李峰认为,周人灭商不仅是一场军事战争,也是一场意识形态甚至心理上的战争。因为商纣王被冠以昏庸残忍的暴君之名,商王朝官员也是嗜酒成性、放纵无能,作为天命所归的周人,自认为有难以推卸的责任执行上天对商的惩罚。如《诗经》所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周人自认代表着一套新的道德,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周人当时很弱小,一看商王朝这么强大又这么残暴,就必须在武力之外辅以德,才有可能团结更多的力量,建立强大的联盟,才有可能克商。”宋江宁说。考古对于“殷周之变说”最直接的证据,是周人遗址中从未出现过人殉、人祭的遗存。与商朝同时的西岐小国,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统治方式和信仰结构。“王国维先生那时候绝对看不到这样的证据,这是今天我们考古学能够做的贡献。”宋江宁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王震中曾经总结,商周两代礼制思维分别是注重“人神关系之礼”和“人际关系之礼”,从周初开始,周人——特别是周公——将对天的虔敬纳入礼制框架,提出敬天保民的理念,将“人神之礼”改造为“人际之礼”。王震中认为,实现这一改造最重要途经,就是引入“德”的理念和规范,形成天命与德治、天命与民意相结合的辩证统一。相较于商代的神权政治,这显然是一个飞跃性的进步。
周人将敬天保民的思想贯彻在执政中,比如“明德慎罚”“知稼穑之艰难”“知小民之依 (痛)”等,与商朝的人祭传统等相比,周人在尊重生命、体恤生民方面走出了重要一步。许倬云认为,周人提出的“天命”观念,可以引申为两点:第一,统治者的治国必须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第二,超越的力量,亦即上天,对于人间秩序有监督与裁判的权力。这些观点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突破,摆脱了宗神与族神的局限,转化为具有普世意义的超越力量。统治者承受天命,就要负起天命赋予的道德责任。
“这是高超的理想,很难在真实的人生完全实现,但正由于有此理想,人间秩序的境界得以提升。”在《西周史》中,许倬云称赞道,“周人悬此理想,可谓中国文化上划时代的大事,不像别处以神意喜怒为标准的文化,要经过长时间的演变才走到这一步。”这一套新哲学,安定了当时的政治秩序,引导了有周一代的政治行为,也开启了中国人道精神及道德主义的政治传统。
奠基华夏文明
回到1976年凤雏村发现的那座甲组建筑基址,建筑里最神秘的部分,就是那个作为甲骨坑的窖穴。
这个长方形窖穴位于西厢房第二个房间里,长1.55米、宽1米、深1.9米,上段四壁为1.3米的夯土,属于房屋的夯土台基,下段为0.6米的生土。这个构造说明窖穴打破了房屋台基,时代应晚于房屋台基的年代。窖内东西两边还各有一个纵深 1 米左右的横向洞室,北边有一个小龛。
提到甲骨文,人们想到的几乎只有殷墟,其实周人也有用甲骨的习俗。其材质特点和字体风格,与安阳甲骨都有很大区别。许多刻字小如粟米,细如发丝,最小的只有1毫米见方,堪比微雕,用放大镜才能看清。而直笔刀法刚劲有力,圆笔运用自如,有独特笔风。
周人用这些甲骨来祭祀和占卜,例如其中一片上刻着“伐蜀”,另一片刻着“征巢”,应该是为征伐蜀、巢两国事先所做的占卜。卜辞中记载了关于周人的很多一手信息,比如周人会祭祀去世的商王,说明他们臣服于商人的地位;而“楚子来告”的表述,俨然是一方霸主的口气,说明周人的实力正在上升。负责发掘的周原考古队推断,这些记载中有很多是武王伐纣之前的先周历史。
这些甲骨文体现的语言文字水平,与殷墟甲骨文类似。然而到了西周时期,铸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则呈现出周人在语言文字能力上的巨大跃迁。现存至少有数百篇西周青铜铭文相当长,内容已经十分完整。幸而有这些今天看来歪歪斜斜的甲骨文和青铜铭文,由于古人对于文字的虔敬和信仰,让后世的人们得以重返真实的历史现场。与传世的上古文献相对照后,传说与信史的分野显现出来。
如果说利簋对武王灭商的记录尚显得简明扼要,那么另一些青铜铭文则呈现出丰富而生动的细节。周朝的铸铭青铜器很多用在祭祀祖先的宗教场景中,但内容却通常与祭祀本身并无关系,而是记载了一些真实历史事件,主题相当广泛,涉及周王命令、军功、官员、婚姻、家系宗谱、经济交易、外交和法律条约等方方面面。“比之商代,书写证据在质量上的提高,可以使我们对西周的政治和礼仪制度以及社会状况等方面有更好、更连续的理解。”李峰说。
读写文化的扩散并不限于地理层面,同时也延伸到西周各社会领域。不同于商朝主要用文字占卜,西周的政府行政、官员任命等活动都会付诸文字,西周王畿出土了百余件册命金文,便是当时的任命文书。根据青铜铭文显示,当时在竹、木等材料上的文字书写,已经被用在民间商品交易、土地定契等方面,这些文字虽然早已随着易腐材料化为泥土,但曾经广泛存在于周人的日常生活中。
因为文字在社会中的广泛应用,可以推想,读写能力在西周得到了更大范围的普及,这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易经》《尚书》和《诗经》部分内容便是由西周的人书写,中国真正的书写传统从此起步。周朝贵族从渭河平原向偏远地区迁移,可能同时带着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商朝遗民,文字和文化被播撒到更为广阔的地区,西周因此成为中国乃至东亚文字书写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
“西周的文化对后世影响很大。比如礼乐文化,我们后来认为华夏与戎狄之分就是礼乐文化之分,何为华夏?礼乐文化就是华夏文化的核心。再比如政治的影响,周制与秦制成为塑造后世的两种政治模式。诸子百家更不用说了,中国文化的内核和基础都在于此,儒家就是以周公作为奠基人的。《诗经》更不用说了,奠定了文学的基础。所以我们经常讲,周文化某种意义上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徐良高说。
商文化的显著特征是消灭与取代,周文化则以联盟和兼容为特征。“总的感觉,商文化的传播犹如肯德基快餐连锁店,全球一个标准。而周文化的传播犹如中国的川菜菜系,在不同地方都有所变化,以适应各地人们的传统口味偏好。”徐良高说。
从考古学视角来看,西周国家的形成可以视为一个渭河流域以外的那些带有强烈本地传统的各个地区植入周人精英文化元素的过程。自西周中期以来,周文化传统和不同地方传统的最终融合,为东周繁荣的地方文化奠定了基础。
1963年,在距离周原遗址不远的宝鸡市陈仓区贾村,考古人员从地底发掘出了一只西周青铜尊,名为何尊。何尊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外表张扬繁复,十分精致。尊内底部铸有122字长篇铭文,这篇重要的文献讲述了周成王迁都洛阳成周之事,最引人瞩目的,则是铭文中出现的四个字——宅兹中国。
这四个字的意思是,武王克商之后,向天昭告要建都于天下之中,治理民众。“宅兹中国”象征获得天命,拥有天下。所谓“中国”,并非指代国家,而是指代天下之中的区域。然而因为其字面含义,它被赋予了不可替代的意义:这是现存所有文字中最早的“中国”二字。
从文献来看,中国的称谓,正是始于西周。当然,彼时的中国与今天的中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然而隔着历史回看,那个遥远又苍茫、神秘又壮阔的远古时代,在骨子里与我们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以崇德和平等的信条联合盟友,开创波澜壮阔的逆袭神话,又以接纳和包容的姿态融合异邦,走出不可思议的文化跃迁之路。如此种种,对三千年后的世界仍旧不无启迪。
参考资料:李峰《西周的政体》 《早期中国:社会与文化史》;许倬云《西周史》 《万古江河》;徐良高《由考古发现看商周政体之异同》;韩茂莉《大地中国》等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