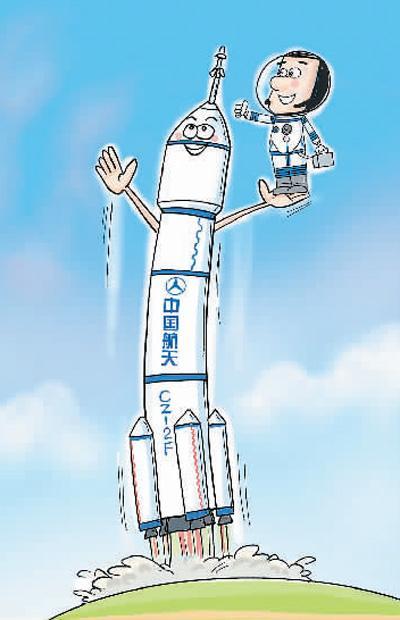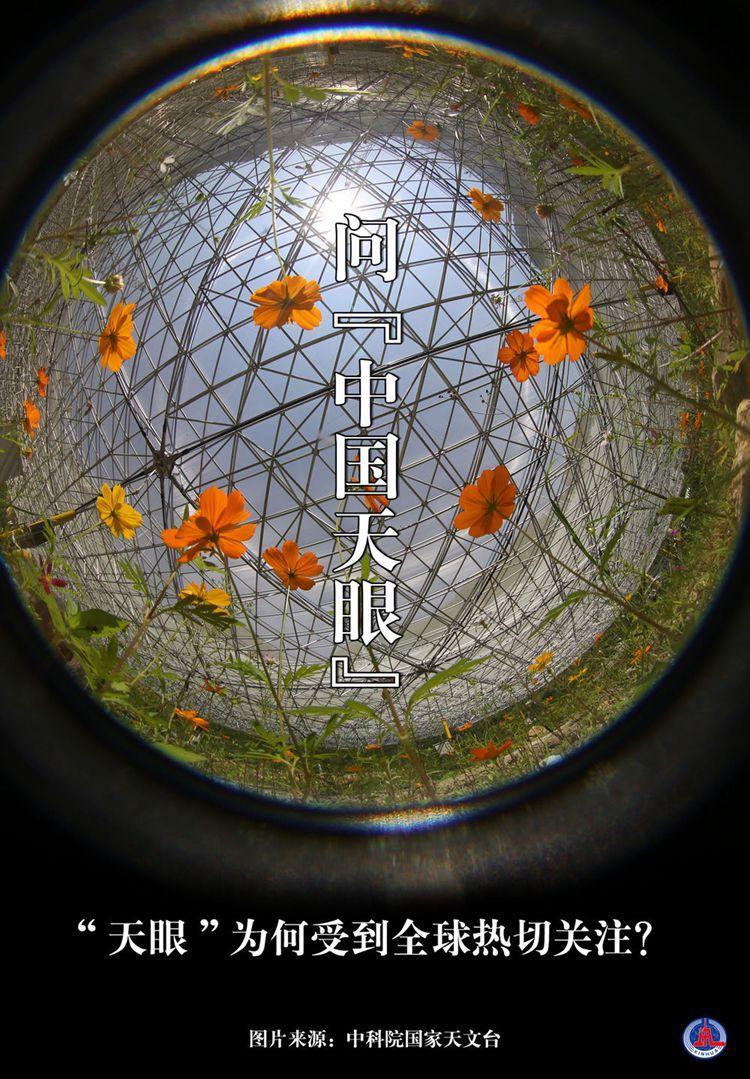21世纪初,澳大利亚遭遇的严重干旱启发学者发明了“乡痛症”(Solastalgia)一词,用于描述环境变化对人类造成的痛苦

许多自然景观其实都是人类工程的成果。
新浪科技讯 北京时间7月17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乡痛症”(Solastalgia)堪称21世纪的一大重症,但大多数人却对这个词闻所未闻。其症状包括:心底总有一种迷失感,隐隐觉得自己与故土相剥离,总觉得自己像个异乡人,从未离家、却又有种思乡的情愫。你可能不了解此病的大名,却有过这样的感受。而如今人类创造了一个自己不愿在此长居的世界、一个缺失了大自然的世界,“乡痛症”的痛苦自然也难以避免。
大自然在飞速离我们而去。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数据显示,全球野生脊椎动物已有一半在过去四十年间灭绝。超过2.9亿英亩(1英亩≈4046平方米)的北美草原已被转化成了农业用地。按目前的增长速度,美国的森林面积到2050年时将减少3千万公顷。在2000至2030年间,生物多样性重点地区的城市用地面积预计将增加三倍。
我们都知道,这些表象的背后还潜伏着更深重的灾难。去年冬天,北极温度竟未下降到结冰点。《巴黎协定》实施不顺,气候变化也屡屡造成意想不到的恶果,如南极的巨大冰山脱离冰架、大堡礁发生严重白化等等。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在人类一手打造的未来世界中,自然的参与将急剧减少,生物多样性也将严重受损。
这为人类带来了一个新问题:大自然与我们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如果摧毁了自然环境,将使我们自己痛苦不已。2003年,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环境与生命科学学院的环境哲学家格伦·阿尔布雷奇(Glenn Albrecht)提出了“solastalgia”(乡痛症)一词。就像nostalgia(乡愁、怀旧)一样,“solastalgia”也是个很难准确定义的概念,但一说出来大家都懂。阿尔布雷奇写道:“solastalgia是指失去自己家乡环境、或无法从中获得慰藉的苦痛之感。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深爱的家园正在受到侵害,便会产生这种感受。”这些“侵害”的形式不同,力度也不同,但在意识到家园受侵后产生的失落感和不安感总是同样强烈。
阿尔布雷奇选择“Solasta”作为“乡痛症”的词根有两层原因。“Solasta”既能引申出“solace”(慰藉),又能引申出“desolation”(孤寂)。“nostalgia”可指乡愁或怀旧,都是对其它地点或时间的渴望;而“solastalgia”则是对如今所在之处应有面貌的渴望。比如说,在自然已不复存在之处渴望自然。
如今这种心态已经成为了主流。每一代人都有相应的小团体跳出来反对愈演愈烈的环境灾难,如嬉皮士和一些小型政治与宗教团体等,但它们仍属于亚文化现象。大部分人还是在驳斥自己并不理解的科学理论、假装地球并未变化。如今,自然秩序的瓦解已经不再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因此,我们急需找到某种新的慰藉,还需要相应的市场来满足这种需求。
酒店大堂中的“自然”似乎比真正的大自然舒适得多。首先,严寒是不存在的。大堂中总像夏令营一样舒适宜人。“大起居室”(Grand Living Room)就像一座巨大的木屋。里面有壁炉,点着天然气生的火。人造石头时而还会发出人工合成的狼嚎声。酒店前台旁边的动画场景总能立即吸引孩子们的视线:一头机器麋鹿、机器熊和一棵机器树正聚在一起“聊天”,只要孩子们按下按钮,穿着芭蕾舞裙的熊就会大声宣布:“这是整个北方森林中最有魔力的地方。”麋鹿也会跟他们打趣:“你可以随时随地戴在脸上的是什么东西?是微笑。”
这就是大自然消失后、“自然”的模样。孩子们看着这些机器人说话逗乐,与此同时,他们的父母正递上信用卡。在酒店前台底下,一只小小的机器人松鼠忽然探出头、发出一声尖叫。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简直不能更蠢:孩子又按了一下按钮,松鼠又探出头、发出尖叫;然后孩子又按了一下按钮,松鼠又探出头……这种蠢事不断循环往复,可见孩子有多喜欢这只松鼠。对孩子们来说,这里就是天堂。是一处充满了“乡痛”情绪的天堂。
“乡痛症”这一概念最早源自澳大利亚的重大干旱。这些干旱提供了气候变化会影响心理健康的直接证据。其中原住民、直接接触气候变化的科学家、以及土地被毁的农民所受的影响最为强烈。2006年,同在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就职的公共卫生学者尼克·希金博瑟姆(Nick Higginbotham)和同事们提出了一套用来衡量“生态系统扰动造成的生物、心理与社会代价”的评估量表,名叫“环境痛苦量表”(EDS)。他们将“乡痛症”定义为“某人所在的物理环境(即家乡)受外力影响、导致其身份认同感、生活幸福感和掌控力下降”后的一种典型反应。评估方法为询问受试者“我怀念之前在这里感受到的平和与安静”、“熟悉的动植物不断消失,这令我很难过”、以及“一想到我的家庭正被迫离开这里,我就感到很悲伤”之类的问题,问他们是否赞同这些说法。
希金博瑟姆发现,按该方法评估的“乡痛症”感受与其它环境受破坏相关的情绪呈强相关性,如恐惧和愤怒等。因此研究人员总结道,乡痛症似乎“明确表达了人们受环境变化引发的痛苦。”希金博瑟姆发表论文至今已过去了十余年,期间研究人员在全球范围内都发现了环境变化影响精神健康的实例。例如,拉布拉多的气候变暖使当地居民产生了乡痛症;中阿巴拉契亚地区山顶采矿对山峰和山间溪流的破坏也引发了乡痛症。此类例子比比皆是,不一而足。
加拿大环境心理学家曾在2016年指出,气候变化引发的洪水和干旱“常常会导致焦虑、震惊、抑郁、悲伤、绝望、麻木、产生攻击性、睡梦难安、人际关系障碍、急性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症、药物滥用和自杀等情绪和行为。”在亚洲地区,精神病学家注意到温度上升与自杀行为有所关联。2013年一项涵盖60项研究的数据分析发现,全球气温的每一个标准差对应着人际暴力增长4%、群体暴力增长14%。2015年,全球最前沿的医学杂志《柳叶刀》成立了“健康与气候变化委员会”,将“乡痛症”描述为“人们在土地受到破坏、变得不再宜人、且失去了发展机会后的感受”,并将其列为全球精神健康的关键内容之一。
乡痛症是一种新近出现的人类“疾病”。且就像其它疾病一样,也亟待进行治疗。
大狼屋度假村开出的药方是模拟大自然。这种做法其实由来已久。早在1863年,护理学先驱南丁格尔就在《护理札记》(Notes on Nursing)一书中记载了让病人透过窗户向外远眺、欣赏“万物之美、万物之多样、尤其是明艳的色彩”的积极影响。南丁格尔认为,在病床边放置有自然元素的东西可帮助病人早日康复。事实也的确如此。无论以何种方式接触大自然,都会对健康产生明显的益处。如日本的一项研究指出,透过窗户远眺森林有以下好处:1、显著降低舒张压;2、显著增加副交感神经活动,同时显著减少交感神经活动;3、显著降低心率。
自1982年来,日本农业、林业与渔业部便一直在推广“森林浴”。该方法的确具有一定效果:受试者唾液中的皮质醇(又名压力荷尔蒙)、以及心率和血压均有所减少。
1984年由罗杰·乌尔里希(Roger Ulrich)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与整天对着白墙的病人相比,手术后能享受到窗外风景的病人总是恢复得更快。他们“手术后住院的时间更短,护士给出的消极评估结果更少,服中强效镇痛药的剂量更低,且轻微术后并发症的风险略低于其他病人。”在该研究的激励下,很多办公楼开始在室内设置模拟自然风景的动画,让员工感到更加放松。此外,精神病院也从多年前就开始通过改造地形、取得了一定的治疗效果。
公共卫生专家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发现了绿意盎然的环境与幸福感之间的关联:“有大量证据显示,能够接触‘自然’的住宅对人体健康有多种好处。”英国2015年开展的一项健康调查发现,即使在修正社会经济与污染因素后,居民健康仍与当地环境的优美程度呈正相关性,且“环境优美”并非仅与绿地面积有关,研究人员据此总结,“环境的美学水平对居民健康的影响也许比之前预想的还要大”。
然而,我们还不确定大自然为何如此有益于身心健康。有些人认为,森林浴对健康的积极影响要归功于树木所含的芬芳精油。但病人仅仅眺望风景也能更快康复,这又从何解释呢?显然,生物多样性并非其背后的必要条件。
要理解人类如何解决对自然的渴望,不妨看一下尼亚加拉瀑布,它可以说是人类产生乡痛症、进而寻求慰藉的鼻祖。奥斯卡·王尔德在1882年造访该瀑布时,将其描述为“最先令新娘们失望的事物之一”。即使它早已失去了“蜜月圣地”的光环,如今每年仍有1200万游客造访此地。这里的自然景观也招来了许多人造“奇观”,如走钢丝的人、招徕游客的叫客员、玛丽莲·梦露、现在更是建起了赌场。
尼亚加拉瀑布体验的核心是对自然的敬畏。与其无与伦比的体量和规模相比,人类的肉体、虚荣和拼搏竟显得不值一提。这种崇高感足以令人受到灵魂的洗礼。它让人类充分意识到,在这样的自然尺度面前,人类是多么的脆弱渺小。
但尼亚加拉瀑布的讽刺之处在于,这种体验的崇高感和人类在自然面前的无力感,其实恰恰是人类工程造就的效果。瀑布倾泻而下的水量需受“国际联合委员会”的管控。在1950年的《尼亚加拉瀑布协议》(Niagara Treaty)中,该委员会规定了尼亚加拉河的多少水量将用于水力发电和其它用途,以及多少水量将用于景观展示。每年4月1日至9月15日为旺季,期间从早八点至晚十点,瀑布每秒倾泻的水量多达10万立方英尺(约合2831立方米);淡季水量则为其一半。
5500年来,尼亚加拉瀑布一直在自然的作用下不断侵蚀。这对瀑布两岸以此谋生的人而言当然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在1969年,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决定借人力抵消自然之力。他们先是在河中架起了一道防水堰,自1848年3月发生的冰塞以来,这还是尼亚加拉瀑布头一次“枯竭”。在重见天日的瀑布底部,他们发现了成百上千万枚硬币和两具尸体,其中一名女性尸体的无名指上还戴着一枚刻着“勿忘我”字样的戒指。
工程师们对样本进行分析后发现,由于水电站分流减少了水流量,瀑布受到的侵蚀已经降到了最少。但作为工程师,他们还是想证明自己有改造瀑布的能力。于是他们在1973年向尼亚加拉瀑布两侧的居民分发了22万份宣传册,欢迎大家投票表决。宣传册上列出了几种改造瀑布的选项:移除瀑布底部的碎石堆、增加水流量、改变瀑布下方“雾中少女池”的高度、或者不作任何变化。结果当然是明摆着的:绝大部分人都选择让瀑布保持原貌。毕竟,自然景观怎么能和照片上的模样不同呢?
要承认“乡痛症”的存在,最直截了当的方法之一,便是承认人们企图从中复原的行为。“人们总想与充满生机的环境建立起有机联系,一部分原因是人们希望找到一处与其它生物都息息相关的家园、以此解决乡痛症的困扰。”阿尔布雷奇在2006年的论文中写道。为维持尼亚加拉瀑布的自然性,人们选择保留其外貌不变。而这种行为却恰恰与自然想要侵蚀它的意愿背道而驰。
如今,尼亚加拉瀑布的美化工作仍在不断进行,只是显得越发浮夸。水雾与瀑布在夜间成了灯光秀的绝佳布景,而灯光秀刚斥400万美元巨资进行了翻修。在人类发明电力照明后,尼亚加拉瀑布成为了人工照明的首批对象之一。灯泡于1879年发明,同年就用在了给尼亚加拉瀑布照明上。如今,这里不断变幻的光线已成为了自拍的绝佳背景。大自然还是要配合照相机,纵使照相机已经升级成了手机,这条金科玉律也变不得。
人们在尼亚加拉瀑布不仅可以用手机自拍,还能玩游戏。2017年,Pokémon Go风靡全球,用户一度多达5000多万,有十分之一的美国人都在玩这款游戏。2002年的一项英国研究发现,8岁以上的儿童辨认宝可梦精灵的能力远比辨认当地动植物强得多。
研究人员据此提出警告:“有证据显示,自然知识的欠缺与人和自然界的日益割裂有关。”但还不仅于此。生物学家E·O·威尔森(Wilson)曾提出“亲生命假说”(biophilia)的概念,认为人类天生便有亲近自然的欲望,而“精灵宝可梦”便是例证之一。尼亚加拉瀑布含有自然的崇高感,并以此牟利;精灵宝可梦体现了人类热爱生命的天性,并以此牟利;大狼屋度假村主打户外体验,并以此牟利。它们在实现了自然界种种益处的同时,又避免了自然界的一大缺陷:变化和衰退。
对自然的美化也使得自然成为了“一剂良药”。“自然”在我们心中已不再是“雄伟壮丽”的代名词,而是变成了游乐场。我们不再试图与大自然对抗,而是想在其中舒缓心境。既然真实的自然无法提供慰藉,我们就开始从“人造自然”中寻找慰藉。自然的娱乐意义已经取代了原本的荒凉意味。这个市场十分高效,我们可以从市场创造的对自然的渴望中、买到解决“心病”的药方。
人类文化的这一改变是好是坏暂且不提,我们若想存活下去,就必须如此。一项针对澳大利亚受“乡痛症”折磨的原住民的精神评测总结道:“如今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加强适应性’。”精灵宝可梦、尼亚加拉瀑布和大狼屋度假村都是我们进行适应的例证。人类的聪明才智是造成眼下灾难的根源,但也找到了一种解决与自然的割裂感的方法。既然我们难以停止发展、阻止气候变化,就要寻找更简单的方法,例如“与自然重修旧好”。
人类一直梦想着与自然界和解。英语中天堂“paradise”一词的词根为波斯语中的“Pardes”,意味“带围墙的花园”。圣经《创世纪》讲的便是一男一女被逐入受苦受难的尘世、希望通过自身努力“让地面上的一切变得宛若天堂”的故事。这个梦想如此美好,许多现实世界的意识形态中都有它的影子。所有乌托邦式的世界中,人类的欲望都能够与自然秩序和谐共存。但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的统治范围甚至已经超越了统治自然带来的迷茫感,人类已无暇去想这个问题。“自然”曾一度被视为人类最终的栖身之地,如今却也不是非此不可了。
如今,与自然和解的梦想正在我们的见证下逐渐消亡。这也是现代人产生“乡痛症”的原因之一。我们选了一条更简单的和解之路:通过机械改造自然,而非控制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们拒绝把这个伤痕累累的世界视作自己的家园,宁愿建起一座座粉饰太平、肥皂泡般的所谓“天堂”。
清晨时分,孩子们仍在熟睡之中。此时的大狼屋度假村堪称一处平静的所在。大堂里的卡通布景如真正的树林般沙沙作响,没有孩子按下按钮、让机器动物们大吵大嚷。一只机器鸟儿时不时高唱几声。四周竟真如大自然一样安详静谧,让你想起身处湖畔或林间的感受。但这种回忆只会令你更加感伤,因为它终归只是回忆而已。在享受这种模拟出来的自然之乐时,心中总难免感到一阵刺痛。(叶子)

了解更多信息 欢迎关注科学探索微信公众号及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