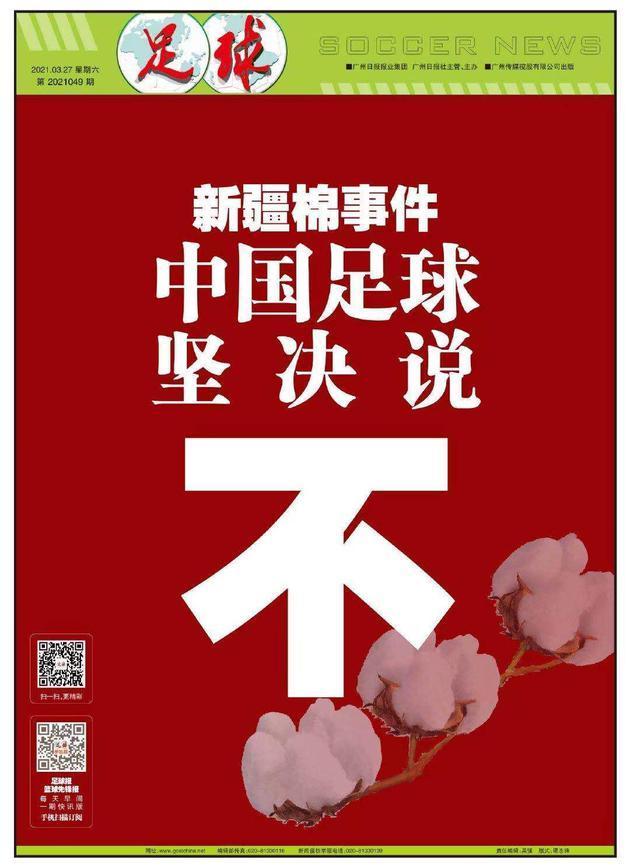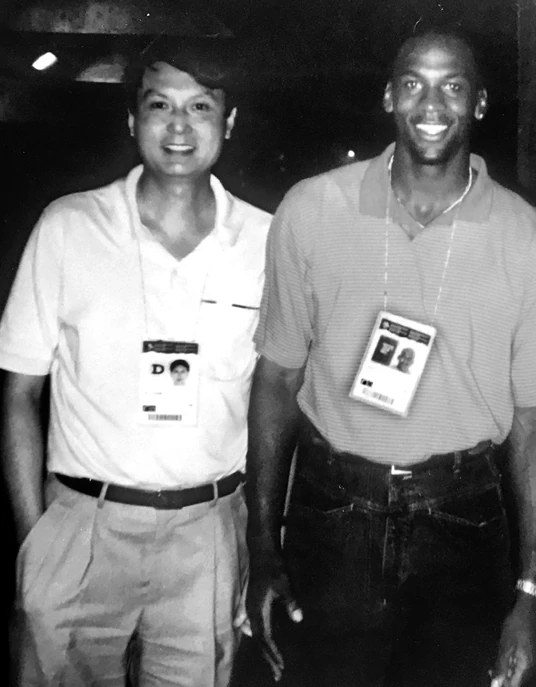资料图。
进入9月,天津市海河教育园体育中心体育场里,几乎每天都有精彩激烈的体操“大PK”上演。全能大战中,力与美的集中爆发,更是将人们对体操的关注推向高潮。
一年前的里约,中国体操队首次遭遇1984年重返夏季奥运会以来的“零金牌”,一年后的天津,虽然“里约之殇”的警醒犹在,但林超攀、邓书弟等运动员完美的动作、坚毅的眼神,让人们对中国体操的“东京之约”拾起信心。
体操是中国体育的传统优势项目,不少体操明星甚至凝结了人们对于奥运的诸多记忆。远一点的比如李宁、李小双、刘璇,近一点的比如刚退役不久的杨威、陈一冰、程菲等,他们创造了中国体操的无数传奇。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李宁被选中点燃圣火,更被看作是对中国体操的最高加冕。
人们习惯了一直处于高光中的中国体操,才对里约的“零金牌”一时难以接受。经过这一年来诸多大赛的历练,中国体操主力队员从技术到心态都有明显进步,他们在全运会赛场上的精彩表现就是一次极好的检验。
纵观时间轴,现在的中国体操正慢慢爬离低谷。现行体操规则的转向带来的压力和挑战得到了一定的承接和消化,本届全运会体操团体比赛赛制首次向奥运会靠拢,采用了6-4-4赛制,即每队有6人出场,4人上场参赛,4人的成绩将全部计入最后的总分。这为适应2020年东京奥运会更为严苛的团体赛赛制提前做了铺垫。
以“练”为主、参赛较少,导致这支整体比较年轻的队伍无法得到足够锻炼。就国内而言,体操比赛只有全锦赛、全运会、青运会等传统赛事,即使进入国家队,每年的参赛机会至多三四次。
反观美国,据广东体操队一位教练透露,体操季开始后,一个月的比赛就有三四场,美国体操运动员一个月的参赛量,轻松超过国内一般体操运动员一年的参赛量。
面对体操项目在国内影响力的逐步下滑,伦敦奥运会“五环王”邹凯直言:“体操好像只属于奥运会,平时的关注度很低。”项目关注度和影响力的下降,加之传统体操培养模式的局限,让后备人才的隐忧逐渐凸显。
国家体操队领队叶振南说,国家队和省级队之间的人才输送缺口巨大。现任国际体联副主席罗超毅曾担任8年的国家体育总局体操管理中心主任,他更是严肃指出:“目前我们2020年的体操后备人才只有二三百人,是否能达到2024年都不得而知。”
青少年体操人才培养,不能全靠专业化体制,还需加大社会普及与培养,这已成为业界和学界共识。在近几年的探索和尝试中,也逐步明晰了“体操进校园”和“发展俱乐部”两条腿走路的格局。
早在100多年前,著名的英国公学改革就已将体操连同击剑、马术、中长跑一起引入校园。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我国几乎每所中学都开设有体操课,遗憾的是,没能在校园中得以延续。
近几年,国家体育总局多次呼吁青少年参加体操练习,并已与教育部体育主管部门达成共识,将体操作为进校园的7个项目之一,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接触体操,见识其魅力进而喜欢上体操。
国家体育总局体操中心体操部部长王童洁透露,我国目前已开展讨论,以体操进校园等项目为依托,加速改革国家体校制度,逐步将体校纳入正常的教育体系。
“体操对锻炼孩子的协调性、柔韧性和团队意识,培养空间感肯定有好处,但练体操太苦太累了,我有点不忍心。”在体操赛场的看台上,一位年轻妈妈的观点在家长群体中很有代表性。一段时间内,由于社会普及和市场培育付之阙如,苦、累、危险成为体操的代名词,不少家长望而却步。
基于此,3年前,国家体育总局体操管理运动中心提出了“快乐体操”的理念,意在扭转人们的固有观念,让所有人都能参与其中,真正撬动人们对体操的热情和兴趣。
2017年里约奥运会上,美国选手西蒙·拜尔斯狂夺4枚金牌,她谈及成功原因时所说的那句“享受比赛、享受体操”,可以看作是对“快乐体操”的一个注解。
“快乐体操”概念推出后,包括制定快乐体操器材标准、俱乐部标准、教练员管理办法等基础文件的基础工作早已完成,并设计1至10级的等级锻炼标准。在推广过程中,也积极借助融汇社会力量进行市场化运作。据了解,快乐体操俱乐部在全国已开设有几十家。
“体操爱好者不断增多,肯定会夯实并扩大这项运动的‘塔基’,也只有在此基础上,再加上通畅的上升渠道,才能确保金字塔‘塔尖’永远星光闪耀。”一位地方队教练说。
8%的参与率、4000家俱乐部,对于这两项衡量体操运动普及化及发展水平的指标,我们还有不小的差距,但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也意味着,推广体操运动、培育体操市场,我们尚有不小的空间可以挖掘开发。
敞开大门,敲掉壁垒,期待中国体操重回巅峰。
(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