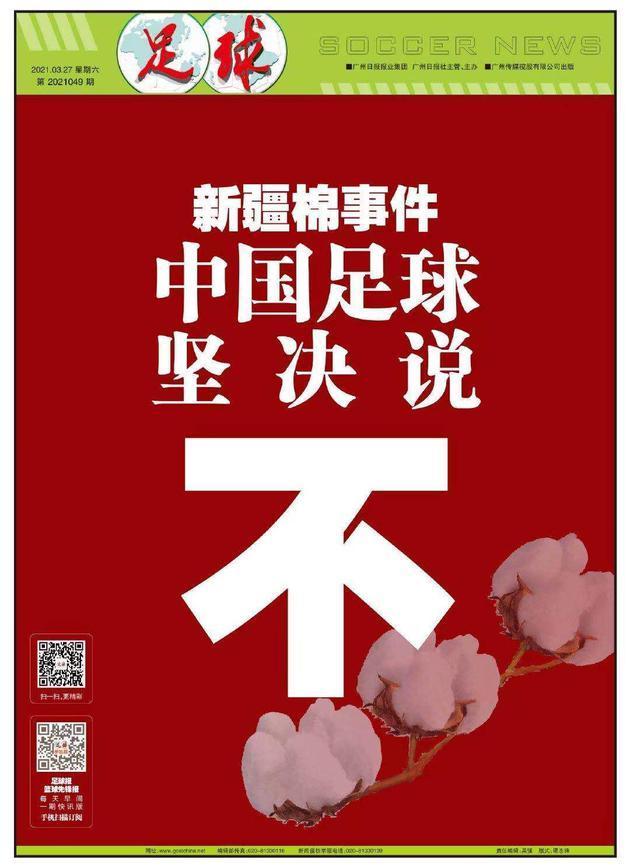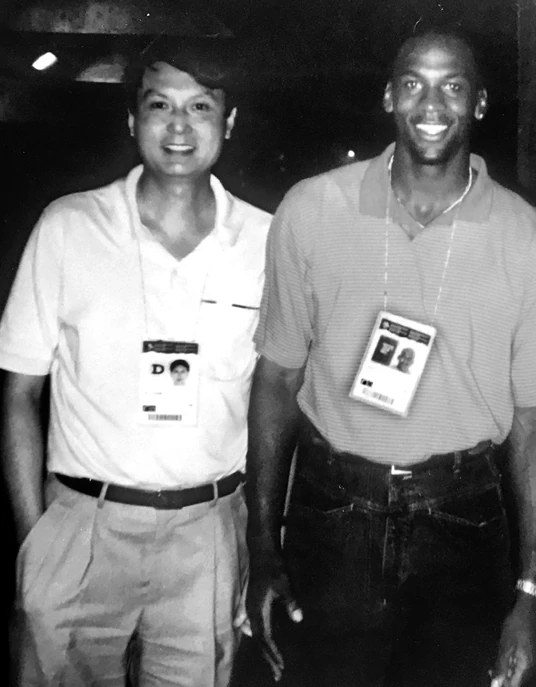原标题:申思袒露希望培养能踢5大联赛球员 为错误承担责任
重获自由后,申思决定先解决一下困扰自己多年的膝关节问题,他动了手术,现在恢复到可以慢跑的程度。平时得空就往健身房钻,踩个自行车、25米的池子游上十几个来回不成问题。在45岁的年纪上,他终于成功避免了堕落成一个油腻男人。人到中年,申思如今时常反省自己年轻时的言行,比如20岁出头那会儿为了“抢逼围”死活要和徐根宝争个高低,“有啥意思呢?”他现在只和自己的身材较劲了。而在时间涤净了曾经的恩怨之后,对于申花,他内心是否还剩下某种可以被称为感情的物质?“两个字,”申思说,“感恩。”

国庆前夕,晨报记者去幸运星足球俱乐部采访了作为老板之一的申思。除去和根宝之间的“恩怨”,我们也谈到了已经去世的王国林,还有其他那些在他前半截的人生中无法回避的人和事。他在这次采访中首度分享了6年铁窗生涯的经历和感悟,申思觉得,这段岁月帮助自己理解了真实的人性,因而终不算虚度。至于未来的路,漫长且未知,他想走得更稳扎一点,有意义一点。因此,除了重获健康的膝关节,还需要一点儿梦想,这个梦想将由幸运星那些年轻球员去实现了……
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是比较善良的一个人
出狱即将满5个月的时候,申思接到了王国林的死讯。去年8月29日晚上,这名昔日中远俱乐部的老总在和朋友踢野球时猝死。在后来媒体对于这场突如其来悲剧的报道中,几乎不约而同提到了王国林人生中一段悲情的过往,即2003年因为最后一轮比赛的假球事件无缘末代甲A冠军。当时参与其中的几名队员就包括申思、江津、祁宏和小李明,他们后来都为之付出了牢狱的代价。事件的环到这里其实已经闭上了,但此后很长时间里,舆论的声音并不愿放弃拷问,就像某篇报道的标题企图引导的一样,“申思永远欠他一句对不起”。
我问申思,直到王国林去世前两人有没有机会达成某种程度的和解,他摇摇头。“我后来和他没什么接触,因为之前合作得也不是非常愉快,仅此而已……”斟酌片刻后他继而说道,“我想对我们每一个还活着的人来说,首先一点,你要做一个善良的人。然后你还要尊重所有的人。如果做到这两点,对这个社会、对身边的人,都是有帮助的。反过来,这个社会也会因为你做到的这两点,给你一个正确客观的评价。”
后面这段话其实在无意中揭示出了某种关于存在本质的真相——即人终归是活在了外部世界对自己的评价里。逝者已矣,活着的他希望将来的人们如何评价自己?“我想,若干年以后,如果说我好的人多一点,说我坏的人少一点,就可以了。”那么,回到最根本的问题上来,他认为自己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觉得自己是比较善良的一个人,也是比较正直的一个人。人活着,要能做到问心无愧,过得了自己心里这一关。”
当一个人为自己犯下的错误付出了应有的代价以后,他或许有理由认为自己问心无愧了。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个秘密啮噬着申思的良心。和他一同参与了那场比赛的江津后来回忆,自己在被专案组带走的那天早上先给申思打了个电话,后者直到下午才回电,说自己被约谈话了,并且“都说了”。这是2010年10月,“反赌扫黑”已经延续了一年,当事人隐约都有预感,那把火迟早会烧到自己身上。事情真的来了,申思倒有了一种解脱感,终于不必再背负秘密走下去了,这个秘密可以被具化为200万元贿金。
他的父亲申平会永远记得儿子出事的这一天。这天老人去世博园参观,回来接到儿媳的电话,说出事了……无须在这里重复申思他们几个牵涉其中的这桩假球案始末了,记住的人会一直记住,遗忘的人是因为他们选择了遗忘。然而在庭审过程中有一个细节之前可能被淹没在铺天盖地的报道中了,那是在全部的庭审程序结束前,法官对申思说,他可以给自己辩护。申思没有这么做,相反他用这段时间对旁听席上的父亲说了一句对不起,“爸爸是个很正直的人,我成为球员,他付出了很多心血,我对不起爸爸,希望以后能尽孝心。”
放弃自我辩护而对父亲道歉,申思当时这个举动是出人意料的。多年以后他这样解释自己当时的行为,“父母培养我踢球,一直让他们感到自豪的儿子突然之间却给他们带来如此大的伤害,一生里最大的伤害。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再怎么样也都是可以挺过去的,可我当时担心他们会挺不过去,这个打击对老人来说太大了。”
一辆摩托加一套两室户分房 是我20岁时的职业梦想
1993年,在申花成立职业俱乐部前,20岁的申思已经进入它的前身上海队,当时是队里最年轻的一个。“这一年(1993年)我们每个月的基本工资一百多块,还有一些训练奖金啥的,像老一点的球员有一千多港币,我们年纪轻的就五百多。因为当时赞助球队的爱克发是个德国胶卷公司,总部设在香港。这一年下来,我的收入已经超过我爸妈了。”每个月去银行兑换总归是桩麻烦,申思的港币就放在家里。
“还没申花俱乐部那会儿,王后军是我们的教练嘛,他跟我们描绘职业足球,说了浅显的一点就是,以后大家一个月可以拿1万元。我后来和朋友说这件事,我说自己进上海队时20岁,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我们队里老队员都有进口摩托车。所以我当时的职业梦想就是能够在23、24岁的时候骑上进口摩托车,然后球队能帮我在曲阳新村分一套两室户的房子。”
申思后来没买摩托车。1996年的一天,他和当时的女朋友骑摩托车出行发生了一次严重车祸。沪上的报纸寥寥几句话报道了这次事故,并没有引起外界过多的渲染。在没有网络的年代里,大家都活得矜持本分,专注于自己眼前方寸世界里的生活。二十多年以后我们旧事重提,他哈哈大笑,这是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唯一一次,说“这辆车还是成耀东的!”那年,他直接买了辆桑塔纳,从此成了有车一族。说起来是很扎台型的,“那会儿,申花队里球员只有三张自备车牌照,给了范志毅、成耀东和我。他们两个是正副队长,而我呢,因为当时在申花踢不着,就要求转会,准备去大连队。为了留住我,俱乐部把第三张给了我……”
赶上“最好和最坏”的时代 我们承担了该承担的责任
一切都是命。申思的职业生涯连头带尾不满12年,却正赶上中国足球最好和最坏的时代。这样的时代成就了他,给予他金钱和名利,并最终摧毁了他。2005年退役后他接受采访,直言中国的足球联赛其实是一个畸形联赛,而自己算是这个畸形联赛中的畸形受益者。今时今日,当一切荣辱都过去后,重新审视自己的命运,生逢这样的时代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
“当然是……幸运要多一些。你看,在我们之前的几代球员能力和成绩不输我们,但社会地位和财富积累这些方面,和我们这一代不能放在一起去比较。这不是因为我们踢得多好,不过是机遇赋予我们的,让我们不仅在足球领域留下印记,更成为这座城市一部分美好的记忆。定格了,再不会被改变了。这是我们最幸运的地方,必须要承认这一点。”但他也承认,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决定了很多错误会相对难以规避。“这事情(假球)一定会存在,这就是足球。我想,自己现在用不着去回避什么东西。反过来说,很多东西也不会因为回避了就不存在。对我们来说,作为这事的一份子已经承担了自己该承担的责任。但在这件事情里,我们不是起主导作用的人,也不是起策划作用的人。”
曾经有很多声音为申思他们鸣不平,认为球员只是身处假球这根利益链底端的人,很多处在更高端的人都侥幸逃过了法律的惩罚,他们几个人等于是担荷了远比自己所作的更大的恶。“很多朋友觉得,我们几个是‘触霉头’。我觉得不是,这是人生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命运的一部分。命运是一环连一环的,在你作出错误选择的时候就要有这份意识,未来有一天应该为此受到惩罚。我们所做的这件事首先不是对的事,这是要定性先定掉的。为此,我不会怪罪这个时代或者其他人,因为这个选择完全取决于你个人,你作出错误决定,就必须为此买单。如果内心还觉得不平,这是是非判断出现偏差了。”
他承认犯了错,但拒绝自己作为一名球员、一个人因为这个错误被彻底否定。“我们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我相信社会公众有自己的判断力,你把这事一五一十地还原,大家会得出自己的判断。或许若干年以后,我们可以再来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参加锣鼓队拿到大学文凭 对这世界的态度更开放了
他是在不经意中看到那个人的,那个活在狱友们传说里的人。申思刚进去就听说过他,“是一个为了一点口粮就去抢劫杀人的人。”
仿佛一扇大门被打开了,门后连着一个他之前连想象都不曾到达过的世界。“我们运动员的生活其实比较单一的,进了监狱以后,以前没接触过的社会阶层,以前没碰到的事情全都碰到了。”也不尽然是坏事,申思说,归根结底还是要看你在里面怎么做人。“我以前踢球的时候在球队里,那是一个男人的世界;进了监狱以后,等于走进了另外一个男人的世界。这两个世界虽然天差地别,但都是由男人组成的,所以有一些规则是互通的。在男人的世界里要让自己被接纳,你首先要像个男人,积累你的口碑。我接触过有些犯人,经常做点‘狗屁倒灶’的事情,背后打打这个那个的小报告,这种男人平时在生活里就让人不齿,那在监狱里也一样被厌恶。”申思在里面的口碑不错,“我也交了些朋友,大家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这些都很正的嘛,这种人怎么也沦落到这里来了呢?”
判决后的第二年,青浦监狱举行了第五届服刑人员运动会。申思在开幕式上一张白褂子红头巾、敲着安塞腰鼓扭秧歌的照片很快在网上传遍了,这是外界唯一一次得以窥探到他在高墙内的生存状态。“我在里面学起来的(腰鼓表演),他们平时会创造各种各样的活动机会,都是自愿报名参加的,但也会有筛选。”在他所服刑的监狱里,每周三是固定的教育日。像他这样报名参加锣鼓队的人,就会跟着专业的指导老师练习,一练一个下午。对于体能的要求很高,所以事先都需要进行选拔。
有些奇怪的是,被照片定格的那个瞬间的淡定微笑,竟然很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他整个服刑期里的一种常态。这有悖于人们的惯性思维,他们想当然地以为那些生活在高墙下的人内心必定是压抑、消极的。申思很久前已经决定,既然这段日子自己必须要去经历,就要尽量过得好一点。“我问过自己,往后这几年的日子注定是黑暗的了,那以什么心态去过?想想还是应该开心地过,过得充实一点。不管是外面还是里面,没有一天应该被白白浪费。他们有那种开放大学,几个专业让你选,有计算机管理啊、物流什么的。我去报名了,最后选的计算机管理,在里面也把大学读出来了,拿到了文凭。看了很多小说,还有英文书。学习之外呢,就积极参加了各种文娱活动和体育比赛。所以我回来以后,亲人朋友看到我的状态都很开心,他们说‘你挺好的嘛!’,这是因为我那几年一直试图保持好的心态。”
在申思看来,这段经历最可贵的一点,是让他成了一个包容度更大的人。监狱是个浓缩的社会,人性的每一面在这个空间被缩小了的世界里都被一一放大、凸现,申思观察并思考着。“我现在特别能理解不同世界观的人,每个人受教育的程度和他生活成长的环境都不同,就导致对同一件事有不同认识。原来我想象不到,现在可以理解了。我谈不上成为了一个更宽容的人,但至少能做到去理解,我现在对世界抱有一种更开放的态度。年纪轻的时候,我的世界观是很狭窄的,很绝对的。”
多年后得到根宝认可 徐指导是一个有胸襟的人
如果是现在的自己遇到徐根宝,他觉得两人之间的矛盾是可以避免的。
“在和徐指导的事情上……当时我们最大的分歧是理念上的差异。徐指导偏英式,抢逼围。我那个时候就喜欢巴萨,当时做的球星卡上面不是要写自己喜欢的球队吗?我写的就是巴萨。我在申花穿14号,因为克鲁伊夫在国家队和阿贾克斯也穿14号。他带巴萨的风格,就是我喜欢的那一路。”根宝有一次问他,是不是对申花踢法有什么想法。“我说抢逼围是肯定对的,但世界上没一支队能自始至终在90分钟里实行抢逼围的。我们肯定要选择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场区进行抢逼围。我另外还提出了一点,就是抢好了球以后我们要做啥?好,那么直到十年以后他再讲出来,‘接传转’。而我当时的理念已经是这样了,抢逼围是要的,但是也要接传转。徐指导觉得那个时候的申花是不需要接传转的,只要抢逼围就行了。是这样的一种分歧,在足球上,这就是很大的分歧了。”
他后来反省这段过往,“或许当时年纪再大个十岁,这事装个糊涂也就过去了,没啥必要。但我当时是小朋友呀,我就较真。足球怎么可以只有抢逼围,只有后卫开大脚传给前锋呢,足球不应该是这样的呀。足球应该是踢 PASS,要接传转嘛。”
根宝是家长制的教练,他要求的不是独立之精神,而是绝对之服从。在他执教申花的年头里,申思始终不得重用。所以当时间来到几年后的2002年,那场直到现在仍被频繁提及的虹口德比中,他在中远进球后跑到申花教练席前咆哮示威的行为就被大部分人理解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复仇。“怎么说呢,当时整座城市都在为这场球疯狂,作为一个亲身参与者,你很难保持冷静。我当然受到的压力更小一点,但作为祁宏来说,全场的球迷都拿着人民币对他挥舞,我相信看到了这一幕,对每个人来说心里都是有触动的。现在想想也是一段蛮有趣的回忆,再也不会有当年那种氛围了。”
后来申思去中邦做教练,有时球队和东亚踢比赛。“徐指导就和中邦老板卫平说,‘你看申思,自己踢球的时候防守不怎么样,带的队防守倒挺好的。’我听说以后就很感触,在我球员生涯里和徐指导合作不是很愉快,但当自己走到教练岗位上,取得一定成绩的时候,作为一个老教练他还是认可我的。”迟到的认可也是一种慰藉,“我们做人,恩怨是一方面,就事论事的态度也是很重要的,这就能看出你做人的胸襟来。”
后半生唯一目标 培养出踢五大联赛的球员
“我踢球的时候不是防守类型的球员,但应该怎么防守,应该怎么去压缩对手进攻的空间这我是搞得清楚的。”申思现在从事青训,和当年带中邦一样,绝不让球员忽略防守这一环。他对于巴萨的热爱一直延续至今,因此幸运星俱乐部从创立之初就坚定了“踢巴萨一样的足球”这个思路。
“巴萨是最讲究传控的球队,他们很多传控的训练方法突出了两条,一是无球时怎么创造空间,怎么把场区扩大;二是一旦控球失误以后队员马上要反抢。这不是靠教练在场边拼命喊‘反抢!反抢!’就行的,我们平时就通过训练场景的反复模拟,要队员自然而然做到快速反抢。像这些一、两年级的小朋友还不太会踢球,但我们已经在和他们强调攻防转换两端速度如何加快,要让它融入到肌肉的记忆里,成为一种下意识的反应。”
申思对于足球还是有激情,讲起青训,眼里竟有光芒闪闪烁烁。父亲申平在他出狱那天对相熟的记者说,儿子回家路上就急不可耐地和祁宏在电话里商量俱乐部的未来运作了。让申思觉得欣慰的是,这家自己参与打造的俱乐部并没有因为他和祁宏受到牵连,他们缺席的那些年里,总经理易文斌和张勇他们坚持了下来,俱乐部的规模也在慢慢扩大,他们如今教练员就有50人左右。“幸运星成立的前十年里,我们培养的球员进了上港、申花,还有国家队,国奥队和国青队。后面十年,我想把我们球员在质量上再提高一下,要培养一些进入五大联赛,和其他欧洲顶级俱乐部的人。对我来说,这就是我后半生最大的也是唯一的目标。人还是应该给自己定一些目标的,这样活着会觉得有意义。
新闻晨报体育